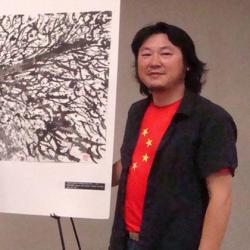??中國人對飲茶場所的講究,在唐代已開其端,至兩宋則蔚為大觀。“杭州城內外,戶口浩繁,州府廣闊,遇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俱有鋪席買賣。蓋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醬醋茶。”城市與鄉野,處處有茶肆。茶肆,也稱茶坊、茶館、茗鋪、茶邸等,是宋代重要的市民公共空間。從《西湖老人繁勝錄》《都城紀勝》《雞肋編》《武林舊事》《清明上河圖》《夢粱錄》等典籍圖畫中可知,宋代茶肆主要有固定茶肆與流動茶肆兩種,前者多位于交通要沖之處,后者主要靠茶販推車、提瓶,穿梭販茶。
??為招徠顧客,茶肆先從裝修上著手。高檔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再以“插四時花,掛名人畫”“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裝點門面。茶肆掛畫種類繁多,不僅有書法字畫,還有名人畫像。司馬光于北宋德高望重,“光歿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以表敬意。茶肆還設棋局,請人吹曲作樂。懸掛名人字畫能帶來廣告效應,可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許多茶客慕名而來,在品茶暢談之余,還能欣賞名流墨寶。懸掛名人字畫逐漸成為茶肆經營的重要宣傳手段。久而久之,人們將品茶與賞畫很自然地聯系在一起。“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蘇東坡言:“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因茶肆與字畫結合,所以越來越多的文人參與其中,茶飲也朝著文人化方向發展。茶肆與畫幾乎形影不離。品位高雅、環境清幽的茶肆,成為士大夫會友的首選之地,“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可見那時的茶肆已然成了一個“花竹扶疏”的去處。
??茶肆還擴展經營類目,按四季或節日需要,增加許多不同門類的消費品,使茶肆經營更加多元化。“四時賣奇異茶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馓子、蔥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還出售各類“涼水”,如“甘豆湯、椰子酒、豆兒水、鹿梨漿、鹵梅水、姜蜜兒、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金橘團、雪泡縮皮飲、梅花酒、香薷飲、五苓大順散、紫蘇飲等”。有時,茶肆會遇到自帶茶團的客人。陸游便曾“裹茶來就店家煎,手解驢鞍古柳邊”。
??除經營茶飲酒菜外,茶肆還會售賣服飾、字畫、文玩之類。《東京夢華錄》卷二中記載:“潘樓東去十字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葉夢得《游石林記》:“余紹圣間春官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為出奇石。余時病臥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若是店面較大,有上下兩層樓,還可提供其他服務。如《夷堅志》“京師浴堂”條中載,有一外地任職的官員本要到吏部參選,但起得太早,吏部還未上班,于是想著先到一茶邸小憩等待,但他沒想到,茶邸中竟是浴室。
??說書藝人在茶肆中搭臺開講,飲茶者一邊品茗一邊聽書。有的藝人長期在某個茶肆表演,茶肆也會因他聞名,或因他講述的某種話本故事而得名。例如“王媽媽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或是因為藝人講述這類故事而得名。在這樣一種寬松、休閑的氣氛中,茶客們邊啜茗,邊聽絲竹、說書,或賞書畫,或觀棋,真可謂“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一處茶肆、一盞清茗,宋人在茶色、茶香、茶趣中營造出詩意空間,使美的氛圍彌漫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見,兩宋的茶肆已不僅是飲茶休息之所,還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交際場合,是家具陳設種類齊全,集飲食、交流、娛樂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飲茶空間。
??梅堯臣在《南有嘉茗賦》中生動描繪了宋人飲茶的風氣:“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賤,亦時啜而不寧。”無論何種職業、階層、性別,都有飲茶需求。當茶肆成為各色人等匯集之所,茶客在茶肆中的見聞與活動,促進了信息的交流與傳播。比如《老學庵筆記》載秦檜的孫女崇國夫人豢養的一只獅貓走失了。臨安府為找到這只獅貓,馬上“圖百本,于茶肆張之”。由此可見,茶肆的影響力之大,輻射面之廣,甚至可以說,茶肆是宋代各種消息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宋季三朝政要》載,南宋寶慶年間,宰相史彌遠為對付政敵真德秀、魏了翁,傳出消息:誰能彈劾這二人,就授予高官。有個地方小官員梁成大,聽說這一消息后,每天跑去茶肆中惡意詆毀真德秀、魏了翁,消息果然很快擴散,史彌遠大為驚喜,擢升梁成大做了言官。為了防止泄密,宋廷還于咸平二年(999)四月下詔:“自今除守關人外,并須著寬衫出入,不得入茶坊酒肆。”不止宋代,歷代多有禁止一定品級官員進入茶坊酒肆等聚集地的命令。如清代順治年間就有“禁止二品以上大員出入茶樓、酒肆、戲園”的規定。
??茶肆只是城市社會生活之一端,卻廣泛地出現于宋代筆記與話本中。宋話本《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官差帶人去抓宋四公,作者特別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門前開著一個小茶坊。眾人入去吃茶,一個老子上灶點茶。”茶肆成為許多故事發生的空間。它是交際行騙之處,在《簡帖和尚》中,和尚交代僧兒送金釵簡帖的重要情節,就發生在茶坊里。正因為僧兒送簡帖之事,直接導致了皇甫夫妻不和,才引出后文騙妻的故事。茶肆也是迸發愛情火花之地,在《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范二郎與周勝仙一見鐘情的地方就是茶坊,他們在茶坊中巧妙互通信息,使故事搖曳多姿。茶肆還是落魄文人士子發跡之地,在《趙旭遇仁宗傳》中,趙旭在茶坊題壁作詩,以為“姓名已在登科內”,卻不想一字之差被皇帝斥責,潦倒度日,后又在茶坊巧遇仁宗,這才青云直上。茶肆更是夫妻重逢之所,在《夷堅志》中,徐信妻在建康夜市的茶肆中休息,意外與前夫相遇。一間小小的茶肆,見證無數悲歡離合。
??直到明清,茶肆依然是小說中常見的場景。《水滸傳》第三回,史進在茶館里向茶博士打聽經略府的情況;第十八回,何濤向茶坊里的茶博士問鄆城縣早衙和值日的押司的情況。茶肆讓日常生活里的細節有了真實的背景。
??茶肆也是失物招領處。宋人王明清的《摭青雜說·茶肆高風》記述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在汴京樊樓旁,有一間別具特色的小茶肆。熙豐年間,有一位李氏客人在此與舊友聊天。臨走時竟將一包金子忘在了茶肆。想到茶館之中,人來人往。他不抱任何幻想,連問都不問一聲便拂袖歸去。多年之后,李姓客人故地重游,經過小茶肆門前時,想起這段過往,便與同行的伙伴聊起了丟金子的事情。他們的對話恰巧被茶肆老板聽見,老板便將二人攔住,上前詢問詳情。當問清李姓客人和那位舊友的穿著后,茶肆老板竟將金子如數奉還。后來,老板又將李姓客人帶到樓上。客人大開眼界——只見其中皆為客人遺失之物,有傘、屐、衣服、器皿等,每一件上都各有標記,封記如故,標注著“某年月日,某衣著官人所遺”。如此拾金不昧之人,堪稱北宋茶肆行業的典范。
??宋話本《陰騭積善》也記述了發生在茶肆里的拾金不昧的故事。店主一番“重義輕利”之話,擲地有聲,潤澤著茶肆中的一脈清氣,彰顯著宋人的氣度和風神。這樣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宋人市民意識的萌芽。
??茶肆作為宋代文化與審美觀念的集中體現,記錄著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審美追求和精神世界,是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一扇窗口,對我們當下如何營造出更多富有文化底蘊且觸動人心的生活與藝術空間,富有啟發意義。
??(作者:谷文彬,系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